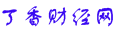上海青莲阁是骗子吗(青莲阁足浴是正规的么)
2023年05月05日 14:01
欧易okx交易所下载
欧易交易所又称欧易OKX,是世界领先的数字资产交易所,主要面向全球用户提供比特币、莱特币、以太币等数字资产的现货和衍生品交易服务,通过使用区块链技术为全球交易者提供高级金融服务。

[作者简介】:王建伟,1979年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代表著作《民族主义政治口号史研究1921-192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另有颇受好评的数十篇专题论文发表。
【摘要】 作为民国北京两处重要的城市空间与商品交易场所,王府井大街与天桥地区代表不同的商业形态,同时也是城市风貌与社会生活的典型展示。不同的空间内部,分布着类型不同、等级不同的商品经营者以及面目不同、阶层不同的各种消费人群。如果说,王府井大街已经成为现代资本主义商业体系在北京的集中展示地,而距此不远的天桥则仍容纳着众多传统社会的流动性摊商、回收旧货的二手市场、经营劣质食品的饭铺、茶楼,以及形形色色的卖艺者与手艺人。王府井与天桥既代表着民国北京,又都不是民国北京的全部,如果只关注一点而忽视其余,犹如盲人摸象,只有将双方平等置放在同一个观察平台,兼顾两者的显著区别,才能对民国北京的时代面相有一个更加全面而深刻的体认。

民国时期的王府井大街
多元性与异质性是现代城市最本质的特征之一,亦是城市研究的基础性问题。城市发展程度越高,内部的差异越大,这种区别通过行政管理、市政设施、建筑景观以及商业网点分布等多种因素表现出来。民国北京正经历从传统国都到近代城市的转型过程,城市形态与功能发生历史性变革,其空间结构、社会结构等亦发生深刻变化。在城市内部,不同群体、不同阶层因经济地位、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差异,呈现不同的生活方式与生存状态,由此生成迥异的城市记忆与城市意象。[①]
一、作为都市新景观的王府井
清代前中期的北京内城是一个政治之城、军事之城,政治属性压倒一切。由于受到政治制度、城市布局以及交通条件的限制,呈现出绝对封闭性的特点。内城中形成了诸多禁令,如不准经营商业、不准有娱乐场所等,绝大多数普通居民只能居住在外城,商业区也多集中于南城,尤其是前三门(即崇文门、正阳门和宣武门)地区,由于地处北京内外城的连接带,地理位置适中,沟通内外城居民的往来,周边地区聚集大量工匠作坊、茶楼和戏园等,形成专门街市,商贸十分繁盛。
民国时期是近几百年间北京城市政治性色彩相对淡化的阶段,是政治性因素不断从中心向边缘退却的过程。从空间维度考察,以往以帝王宫殿为中心的空间结构逐步转向以商业为中心,城市布局的主导因素从权力转向经济。曾经作为帝都象征的帝王宫殿、皇家园林、坛庙,或丧失原有功能而退居幕后,或转换相关用途,成为凭吊或游赏之处。而一些新兴商业场所借助于资本的力量,开始跃居城市的中心位置。
王府井大街作为近代北京一处新式商业空间的兴起,既是一个官方主导、规划的过程,也是一个符合市场规律的自发过程。该街本为旗人驻扎之地,原名王福晋大街,位于紫禁城东华门外南北走向,南达东长安街,北达东四西大街。清代中期之后,随着旗、民分城而居制度的日渐松弛,京师内城不得经商、娱乐的禁令逐渐名存实亡,东四、西单、地安门、鼓楼、北新桥等地出现了一批地点相对固定、时间上具有连续性的商品集市。由于地处出入皇城的重要通道,内务府采购物资也多经过于此,至清后期,王府井地区商业属性开始凸显,不仅有流动性摊商,也有一些固定商铺、饭庄出现,一些昔日王府临街房屋开始经营商业。
东安市场的建成是王府井大街兴起的标志性事件。庚子事件之后,清政府开始在京师地区推进近代市政,王府井所处的东安门外区域成为北京最早进行道路建设的地方之一,“迨光绪末季,值肃王善耆司警政,始以其地改建市场。最初因陋就简,仅具雏形而己。”[②]由于庚子之前,这一带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的街市,因此,在整修道路过程中官方拆除了商贩沿街搭建的一些棚障,选中位于王府井大街北端的原八旗神机营操场,划出部分区域,将东安门外两旁的铺户迁至此地继续营业,逐渐形成了一处每日营业的固定商业场所,得名东安市场。
东安市场是北京城最早的由官方所设的综合性定期集市,采取官商合办的经营模式。《东安市场现办章程》规定,商人任庆泰“禀请工巡总局准其租领立案,发给凭单,官不出款,该商自筹资本建房招商”,“自行筹款先行开沟筑路,次第建造房屋,既建之后,永为己业,不准拆去”,待房屋建成之后,“招至各商在彼营业,既遵警察章程办理。其该商应受保护之利益,工巡局均可承认”。[③]东安市场经营范围覆盖到日用百货、饮食、娱乐等与民众日常生活相关的各个方面。在这个固定的商业空间中,商户的经营者不再像以往在街道上随意,开始遵循既定的社会秩序,服从市场的统一规划和管理。1906年,东安市场北部建立了吉祥茶园,园内每晚有京戏演出,这是北京内城的第一家。内城的人们不用再绕道至前门就可以在此购物、娱乐。随后,东安电影院、会贤球社等娱乐设施在此纷纷开办,进一步增加了王府井地区的客流。宣统年间竹枝词形容:“新开各处市场宽,买物随心不费难。若论繁华首一指,请君城内赴东安。”[④]民初《京师街巷记》记载:“其地址广袤宽敞,初为空场,蓬蒿没人,倾圮渣土,凸凹不平,自前清光绪三十年,改建市场,始惟有百般杂技戏场各浮摊商业等,旋经建筑铺面房屋,其内之街市为十字形,两旁商肆相对峙,曾经壬子兵燹所及,市肆墟燬,不数月,从事建筑,规模较前尤宏阔矣,商肆栉比,货无不备”。[⑤]东安市场的出现具有开创意义,预示着北京城市化进程中消费革命的兴起。
东安市场建成之后几次失火,屡次重建,每次规模都有所扩大,商业益见发达。至1920年代初期,茶楼、酒馆、饭店、戏园、电影、球房以及各种技场、商店无不具备,“比年蒸蒸日上,几为全城之精华所萃矣”:
东安市场为京师市场之冠,开辟最先,在王府井大街路东,地址宽广,街衢纵横,商肆栉比,百货杂陈。……该场屡经失火,建筑数四,近皆添筑楼房,大加扩充,其中街市共计有四。南北一,东西三。商廛对列,街中羼以货摊,食品用器,莫不具备。四街市外,又有广春园商场、中华商场、同义商场、丹桂商场,及东安楼、畅观楼、青莲阁等,其中亦系各种商店、茶楼、饭馆,又各成一小市场矣。场中东部为杂技场,弹唱歌舞,医卜星象,皆在其中。南部为花园,罗列奇花异葩,供人购取。园之南舍,为球房、棋社,幽雅宜人,洵热闹场中之清静处所也。[⑥]
至1930年代初期,东安市场摊商总计已达350余家,其中以书籍、玩具、杂货、糕点、糖果为最多,以社会中上层为主要服务对象,“就是那些水果摊、香烟铺,都带有华丽气派”[⑦]。铺商共计240余家,其中以布店、鞋铺、西装服、洋广杂货商店为最多,“各该铺商之内外—切布置,均极美丽,游人顾客亦均中上级人士,故每日营业尚属发达。”[⑧]由北平市社会局组织编写的《北平市工商业概况》称东安市场在全市所有官办及商办商城中“规模最大,商业亦最为发达” [⑨]。一直致力于收集旧京故闻的瞿宣颖在上海的《申报月刊》上介绍这一时期东安市场的日常状态:
东安市场,当王府大街之中段,距东交民巷甚近,庚子以后所开,其法长街列肆,租以营业,百货无不具备,旁及球场、饭店、茶馆、饮食、游艺之所,乃至命相奇门堪舆奏技之流,皆可按图以索。街之中复列浮摊,以售零星食物花果书籍文玩者为最多,以其排比稠密,人烟繁杂,屡屡失慎重修,最后一次迄今亦逾十年矣。其包罗宏富,位置适宜,有似港沪之大百货商店,而能供日用价廉之物,则又过之。居旧都者,莫不称便。浮薄少年,涉足其中,可以流连竞日,因为猎艳之游,目挑心招,辄复遇之。[⑩]
以东安市场的兴起为发端,王府井逐渐发展成为北京城内最重要的商业中心。由于地处皇城主要进出口的东安门外,靠近东交民巷使馆区,这里成为北京最早开启市政建设的区域之一,1914年京都市政公所成立之后,首先选择了以王府井大街所在的内城左一区为示范区域,开始道路改造工程,包括拓宽道路、房屋基准线测量、整修明沟、铺装工事,修筑沥青道路等。1915年,美国煤油大王洛克菲勒在豫王府旧址上建起协和医院,1917年,中法实业银行在王府井南口建成七层楼高的北京饭店,“道中宽阔清洁,车马行人,络绎不绝。……车马云集,人声暄填,为京师最繁华之区也”。[11]1920年代之后,王府井地区开始设立有轨电车车站,1928年,王府井大街修建柏油马路,交通条件进一步改善。
在东安市场的示范作用下,原本繁盛的正阳门外一批店铺纷纷迁入王府井大街。即使在1928年国都南迁,北平消费市场陷入低迷之时,王府井借助于独一无二的区位优势仍能保持相当水准,“东单崇文门一带地方,距东交民巷甚近,外商林立,各国侨民杂居是处,东城繁荣,乃集于斯。加之东安市场,年来扩充,王府井大街,遂成东城荟萃之地。其富庶情况,不减于昔日之前门大街。”[12]1936年,上海《申报》特派记者在北平观察到,“前门外商铺以资厚牌老胜、所谓北京老住户之购货(尤其衣料),恒以该处购获者为讲究。近年世事推移,此辈老住户大半衰落,前门外之商业已大呈颓势”。而王府井大街则“富丽堂皇”,“其在平市观瞻上几可嫓美上海之南京路,东安市场以小巧玲珑胜,摊肆夹道,百货杂陈,诱惑性且较王府井为甚。故一般顾客,尤其摩登男女,多喜出入其间,外国人之来北平观光者,亦必以市场巡礼为必要之游程”。[13]这一时期,王府井所在的东城已经取代南城,成为北京商贸最为繁盛的区域,《北平旅行指南》对此载:“目前王府并大街、东安市场、西单北大街、西单牌楼,西单商场—带,商业似有蒸蒸日上之势,崇内大街之光陆影院,灯市口之飞仙影院,西长安街新建之新新,长安,两戏院,均见活泼气象,较诸前外大街、大栅栏、观音寺渐有起色。各银行并在东四西四西单及王府井大街,设办事处二十三所,以资吸收储户欵项,而便商民,平市繁华重心,又由南城转移至东西城矣。”[14]
由于地处北京传统的达官显贵聚居地,且靠近东交民巷使馆区与西交民巷银行区,周边富户集中,还有一批外交使节及在京侨民,为王府井的商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目标客户与消费支撑,这一群体的消费品味与消费习惯对王府井的商业业态具有重要影响,呈现出高端、洋气的特点,与北京传统的商业面貌形成了明显差异。此地高档洋行众多,如英商邓禄普、力古洋行,德商西门子洋行,美商美丰、德士古洋行,法商利威洋行等。经营范围涵盖汽车、钟表、电器、钻石、西装等西洋色彩浓厚的商品,在经营模式上亦不断探索,商铺内外装潢高档,商品陈列炫目、考究。外资金融机构如美国花旗银行、法英东方汇理银行、华俄道胜银行等在此开设代理处。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王府井大街都是北京城内最为知名的商业中心之一,引领时尚消费潮流,承担着古都“摩登代言人”的特殊身份。
二、作为平民社会缩影的天桥
“天桥”最初确是一座高拱的石桥,建于明代,位于正阳门外北京城市中轴线南段,为明清帝王祭告天坛时的必经之路,故名“天桥”。[15]从其所居地理位置及名称可见,明清时期的天桥是连接紫禁城与天坛、沟通世俗权力与上天权力的特殊通道,普通人被禁止在桥上通行。从这个意义上说,天桥也是明清北京城整体空间秩序中的一个重要的部件,这与后来它被赋予的底层民俗特征大异其趣。
自建成之后,天桥周边一带视野空旷,环境清幽,是京城士大夫重要的郊野游玩之地。清朝定都北京之后,限令内城汉人及商贩迁往城外,正阳门外商业日益繁华,成为全城重要的商业、娱乐中心。受此影响,至道咸年间,天桥地区陆续出现茶馆、鸟市,一些梨园行人士在此喊嗓、练把式,但尚未形成很大规模。此时,天桥仍是一派田园风光。据曾亲历天桥变迁的齐如山描述:“当光绪十余年间,桥之南,因旷无屋舍,官道之旁,惟树木荷塘而已。即桥北大街两侧,亦仅有广大之空场各一,场北酒楼茶肆在焉。登楼南望,绿波涟漪,杂以芰荷芦苇,杨柳梢头,烟云笼罩,飞鸟起灭”[16]。这种乡野景观很符合久居京城文人们的审美趣味,他们经常在此诗酒雅集,吟风弄月。附近虽有估衣摊、饭市及说书、杂耍等,但为数不多。

民国时期的北京天桥
天桥商业的日渐兴起与清末民初北京城市空间结构变动与市场体系的兴衰密切相关。当地安门、东四、崇文门、花市等曾一度繁盛的商业区域相继衰退之时,天桥则借助于靠近正阳门的区位优势,逐渐吸引一批摊贩以及曲艺、杂技卖艺者,“天桥南北,地最宏敞,贾人趁墟之货,每日云集”[17]。“正阳门街衢窄狭,浮摊杂耍场莫能容纳。而南抵天桥,酒楼茶楼林立,又有映日荷花,拂风杨柳,点缀其间。旷然空场,尤为浮摊杂耍适当之地。于是正阳门大街,应有而未能有之浮摊杂耍,遂咸集于此,此天桥初有杂耍之原因。”天桥市场初具雏形,但“未至十分发达”,“又以京津车站设于马家铺,京汉车站设于卢沟桥,往来旅客,出入永定门,均以天桥为绾毂。而居民往游马家铺者甚多,亦于此要约期会,此天桥发达最早之因。”[18]庚子年间,天桥地区的商业受到一定冲击,但旋即恢复。
民国建立之后,天桥地区的商业功能更加丰富,除众多摊商之外,新增了戏园、落子馆等娱乐场所。“民国元年一月,厂甸改建街道,工程未竣,堆积砖瓦,无隙设摊,当局为谋维持摊贩利益,曾将厂甸年例集会,暂移香厂。时伶人俞振庭者,乘闲于厂北支一棚,演奏成班大戏,并约女伶孙一清串演,原定一月为期。期满,有人援例,移至金鱼池南岸上,赓续其业,未几,再由金鱼池迁至天桥,此实天桥有戏园之始,而同时继起者,亦比比矣”[19]。
1914年京都市政公所建立之后对正阳门实施改造,督修工程处把围绕正阳门月墙的东西荷包巷各商铺房屋以及公私民房约60多处作价收购拆毁,这些工作至1915年基本完成。“而瓮城内两荷包巷商民,则合议将所拆存之木石砖瓦,移天桥西,建立天桥巷,凡七开,设酒饭镶牙各馆,并清唱茶社,暨各色商肆,以售百货,居百工,此又天桥渐成正式商场之始”[20]。
不过,天桥在日渐繁盛的同时,区域内环境也在恶化,“地势略洼,夏季积水,雨后敷以炉灰秽土,北隅又有明沟,秽水常溢,臭气冲天,货摊杂陈,游人拥挤。……由彼往西,地名香厂,夏季芦苇甚多。常年不断秽臭之气,所有商业者皆为臭皮局、臭胶厂,天桥臭沟泄其臭水,与香厂之名实决不相符。”[21]与前文齐如山所述之光绪年代景色已决然不同。
京都市政公所建立之后,平垫香厂,修成经纬六条大街,如华仁路、万明路等,开启了香厂新市区建设,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天桥周边区域的环境:
六年,高尔禄长外右五区。督清道队削平其地,筑土路,析以经纬。同时是区居民卜荷泉诸人,复捐资于先农坛之东坛根下,凿池引水,种稻栽莲,辟水心亭商场,招商营业。茶社如环翠轩、香园;杂耍馆如天外天、藕香榭;饭馆如厚德福,皆美善。沿河筑长堤,夹岸植杨柳。其西南,各启一门,皆跨有木桥。河置小艇,每届炎夏,则红莲碧稻,四望无涯。一舸嬉游,有足乐者。[22]
新世界商场、城南游艺园在香厂地区先后建成,也为天桥带来了大量客流,天桥的经营面积大大扩张,“香厂由草昧慢慢的开化,连带着天桥的面目也渐渐改变起来”。香厂与天桥地区原有的市场连成一片,和平门外马路的拓展也是一个积极因素。1924年电车开通后,天桥成为通往东西城的第一、二路电车总站,“东自北新桥,西自西直门,东西亘十余里,瞬息可至”,“交通既便,游人愈夥,而天桥遂极一时之盛矣”[23]。
天桥地区基本可以分为娱乐场和市场两部分,一般以一、二路电车总站为标志。“在东则率多布摊及旧货摊、估衣棚,北连草市,东至金鱼池。善于谋生之经济家,每年多取材于此。至其西面,则较东为繁盛,戏棚、落子馆为多,售卖货物者殊少”。“其北建有天桥市场,内多酒饭店、茶馆之属,其他营业总难持久,颇呈寥落状况。惟此处收买当票及占算星命者异常之多,亦殊为市场中之特色”。“天桥迤西,先农坛以东,近日成为最繁盛之区域,且自电车路兴修以后,天桥之电车站,更为东西两路之汇总,交通便利,游人益繁”,“即现在该处所有戏棚,已有五、六处之多,落子馆亦称是,茶肆酒馆尤所在多有”。“由此迤西,沿途均为市肆,茶馆为最多,饭铺次之,杂耍场与售卖货摊亦排列而下,洵为繁多之市廛。”[24]
对于北京城里的大多数普通百姓而言,他们在这里能够欣赏廉价的表演,甚至享受免费的娱乐,购买辗转多手的旧货。与此同时,北平正因国都南迁而伤了元气,市面空虚、百业萧条。天桥地区则因定位低端、消费廉价而迎合了特定的消费群体,不仅未受影响,反而日渐兴旺,“近两年平市繁荣顿减,惟天桥依然繁荣异常,各地商业不振,惟天桥商业发达”[25]。《北平旅行指南》也描述道:“艺人如蚁,游人如鲫,虽在此平市百业萧条、市面空虚中,而天桥之荣华反日见繁盛。”[26]
当天桥地区的商业逐渐发达之时,曾经的“天子之桥”的命运也几经波折。清末铺筑正阳门至永定门之间的碎石子马路时,天桥已经丧失原有功能,桥身也为适应马车、汽车通行而降低变成矮桥。1929年,正阳门外大街开始修建有轨电车,天桥变成平桥,但桥栏板仍存。至1934年,为展宽正阳门至永定门道路,天桥作为一座石桥彻底被拆除,此地再无帝制时代的皇权遗迹,其后一直以地名的方式存留至今。
如果说,王府井大街代表了民国北京新兴的商业形态,天桥地区则是另外一种传统模式。此地虽号称繁盛,商家众多,但都为临时性摊贩,设施简陋。民国初年的《天桥临时市场暂行简明章程》规定,天桥市场以维持小本经营为宗旨,“在本市场租地营业者,只准支搭棚屋、板棚,不得建盖房屋。”[27]区域内的所谓“建筑”低矮而杂乱无章,小贩遍地铺陈。在众多来源不同的材料中,对天桥日常形态的描述多有雷同:
站在天桥西头,朝东望,一片高低不平,处处掺杂着碎砖烂瓦的地上,黑丛丛摆着无数荒似的一堆垜一堆垜的地摊,破铜烂铁,零碎家具,古董玩器,以及一切叫不出名目的东西,可是这里的东西虽多,但能够卖上一元的东西,却是凤毛麟角了,在这儿,有许多摆摊的,一见到警察的影子,便眼疾手快,溜之大吉,当然啰,这么着,便可免掏两大枚的摊捐啊。在有摆花生摊的先农市场门前两边,搭着许多补着补丁的破布棚,里面是满塞着现成的衣服,男的,女的,大人的孩子的,以及单的棉的,买估衣的伙计们,不嫌麻烦的,一件件提抖着。[28]
这种观察很具有普遍性,天桥是专属中下层社会的消费空间与娱乐空间,“正阳门外天桥,向为游人麋集之处,一般小商业,及低级生涯,均在该处辟地为业,故有平民市场之称。”[29]那里“游人如蚁”,但“窭人居多”[30]。“很少有绅士气度的大人先生,在此高瞻阔步,到这里来玩的人,多半是以体力和血汗换得食料的劳苦的人们。他们在每天疲倦以后,因为这里不需要高贵的费用,便可以到这里来,做一个暂时的有闲阶级,听听玩艺儿,看看杂耍,忘却了终日的疲劳,精神上得受了无限的慰藉。”[31]各种对天桥那些黑压压的人群的描述也呈现出基本一致的面部特征与精神状态:
天桥是个贫民窟,同时也像一个各种人型的容受湖。四下的人行道上黑压压的头,潮浪般的向这里流,流来的并不静止下来,仍是打这湖的此岸流向彼岸。真的,如果你能在天桥蹓跶一个下午,保管你会遇到这样的情形,同一张脸,刚打你跟前溜走了,一会儿又流了来。在这形形色色的一叶中,看出了有的是因了家庭破产,而失了学的流浪青年,有的是因为受不了官家的横征暴敛,纳不起苛捐杂税,缴不起租价,被生活迫害着不得不放下锄头,打穷乡僻野里跑到繁华的都市来找活作,而又失望的庄稼人。有的是曾在没落途中用过死劲,想还有那些逃灾逃难,无家可归,已沦落成叫花子的男人女人,更有不少的受了掌柜的嘱附,出来取送货物,而偷着来玩会的小伙计们,那些腰间系着条皮带,毫没杀气的武夫们,……在这群各具其面,异声异气的人的脸上,都是深深的刻画着一个在饥饿线上挣扎的创痕,并且表现着无聊,枯寂,不安,忧愁的姿态。[32]
对于众多卖艺者而言,天桥是他们重要的谋生之所,“三教九流无奇不有,百业杂陈无所不备,凡欲维持临时生活者,苟有一技特长,能博观者之欢乐,亦可藉此糊口” [33]。但是,穷人的消费者仍然是穷人,非常有限的铜板基本上仍在这个封闭的空间中实现着内循环,“自前清以来,京师穷民,生计日艰,游民亦日众,贫人鬻技营业之场,为富人所不至,而贫人鬻技营业以得者,仍皆贫人之财。余既睹惊鸿,复睹哀鸿,然惊鸿皆哀鸿也。余与游者,亦哀鸿也。”[34]那些贫困的卖艺者在这里赚取一家人一天的吃食,并在这里消费,然后所剩无几。对于他们而言,“天桥是一部活动电影,是一部沉痛人生的悲剧,虽然,你从他们的脸上,可以看到他们都有笑容。这笑容,是从他们铁压下的心上和身上榨出来的。为了生活,他们便把自己的悲剧来反串喜剧,把自己的眼泪滴成歌曲,自己的技术作为商品,自己的精力变成娱乐。……下层群众的集体,天桥写出了这社会穷苦者的真实面目,匍匐人生道上,流血出汗洒泪珠,是为了生活,是为了应付不断抽上身来的铁鞭,每个人,在这把生命渐渐支还上帝去,他不会知道自己一生是为着什么,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生活。他承认命运,那人骗人的荒谬的语言,使他们不作声息过下这一生。”[35]
天桥既为人烟稠密之地,秩序混乱,往来人员复杂,多有作奸犯科者藏匿其中,“据说侦缉总队是派有很多人,天天化妆在这里采访、侦视,做办案的工作。他们自己说,这里是藏污纳秽的所在。一般下层社会的人,多要在闲暇的时候到这里来玩。凡是做案的人,多不是什么高尚有知识的人。在他们没见过多大世面的人,陡然的得了意外的财富,自然免不了挥霍和夸耀,因此在娼窑和天桥是很好的办案的处所。他们得着这妙诀,所以在这里很破过许多惊人的奇案。还有其他机关,也派有相当的密探。”[36]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严景耀通过调查得出结论:“北京四分之一以上的窃盗罪是在前门外(包括东西车站)及天桥犯的。”[37]
此外,天桥还一直被视为“有伤风化”之地,“顾往游者品类不齐,售技者为迎合观众心理,举动亦往往儇佻,益以脂粉为生之游娼,复假此地为勾引浮薄之所。职是之故,天桥乃不见齿于士林”。[38]在众多知识群体的描述中,天桥代表着粗鄙、杂乱、底层,甚至污秽、肮脏,他们普遍表现出高高在上的俯视心态。
三、摩登与粗鄙:一座城市的两种书写
1918年,李大钊根据他在北京的生活体验描述了当时社会的新旧并存:
中国今日生活现象矛盾的原因,全在新旧的性质相差太远,活动又相邻太近。换句话说,就是新旧之间,纵的距离太远,横的距离太近,时间的性质差的太多,空间的接触逼的太紧。同时同地不容并有的人物、事实、思想、议论,走来走去,竞不能不走在一路来碰头,呈出两两配映、两两对立的奇观。[39]
与此类似的是,瞿宣颖如此概括庚子之后三十年中的北京:
自庚子以至戊辰,这将近三十年中,北京是个新旧交争的时代。旧的一切还不肯完全降服,而对于新的也不能不酌量的接收。譬如拿些新衣服勉强装在旧骨骼之上,新衣服本不是上等的,而旧骨骼也不免失去原有的形状。[40]
沈从文对民国北京的印象就是在不断变化,“正把附属于近八百年建都积累的一切,在加速处理过程中”[41]。正是在一个极短的时间内,社会发生剧变,由此在一个有限的城市空间中表现出诸多冲突与对峙,正如诗人钱歌川在1930年代看到的那样,北平“真是一个怪地方,新的新到裸腿露臂,旧的旧到结幕而居。”[42]无独有偶,同时期的另一位观察者也注意于此:“赤着大腿的姑娘,和缠着小脚的女人并排的立着走着,各行其是,谁也不妨碍谁。圣人一般的学者,和目不识丁的村氓可以在一块儿喝茶,而各不以为耻,如同电灯和菜油灯同在一个房间一样,各自放着各自的光。”以至于作者不得不感叹:“北平有海一般的伟大,似乎没有空间与时间的划分。他能古今并容,新旧兼收,极冲突,极矛盾的现象,在他是受之泰然,半点不调和也没有。” [43]朱自清也曾对此总结:“北平之所以大,因为它做了几百年的首都;它的怀抱里拥有各地各国的人,各色各样的人,更因为这些人合力创造或输入的文化。”[44]后来,作家林语堂也用写实的笔调,概括了民国北京的多元与包容:
满洲人来了,去了,老北京不在乎;欧洲的白种人来了,以优势的武力洗劫过北京城,老北京不在乎;现代穿西服的留学生,现代卷曲头发的女人来了,带着新式样,带着新的消遣娱乐,老北京也不在乎;现代十层高的大饭店和北京的平房并排而立,老北京也不在乎;壮丽的现代医院和几百年的中国老药铺兼存并列,现代的女学生和赤背的老拳术师同住一个院子,老北京也不在乎;和尚、道士、太监,都来承受老北京的阳光,老北京对他们一律欢迎。[45]
作为长期的国都,北京一直是五方杂处之地,新旧、中西、贫富、高低同时存在,从而也比其它城市能够容纳更多如此对立的事物。以王府井与天桥为例,两者作为民国北京非常重要的商品消费与大众娱乐空间,虽然相距不远,但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城市样貌以及区域内人群典型的生命体群像。在王府井大街,已经是一派现代都市气象,一位游客回忆他在1933年游览的感受:
一下车,也许会使你吃一惊,以为刚出了东交民巷,怎么又来到租界地。不然何以这么多的洋大人?商店楼房,南北耸立,有的广告招牌上,竟全是些ABC。来往的行人自然是些大摩登、小摩登、男摩登、女摩登之类,到夏天她们都是袒胸露臂,在马路上挤来挤去,实在有点那个。再向前走,到了东安市场,一进大门,便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香气,沁人心脾,会使你陶醉,陶醉在这纸醉金迷的市场里。到晚上,电光争明,游人拥挤,谁初次来临不感到头晕目眩、眼花缭乱呢?[46]
而夜色下的东安市场则呈现出另一种异常暧昧的情调:
街面给电灯光所反映出的树影是扶疏的,脚踏车、人力车、汽车、混合在喧嚣的一团里。凌乱的排列着几家商店,流露出了一点上海味,然而还摆脱不了北平固有的形态。市场的南口是虚掩的,里面充满了热烈的情绪。一列列的新设的木架上排满着货物,给灯光照得亮晶晶地。时断时续的游女,都在薄的衣上加着短的毛线外衣,秋是显明地证明着是深沉的。转入了另外的一条场面时,迎面荡来的几个全是娇媚的笑魇,浓馥的香气,洁丽平整的服饰的波纹,夏季的汗臭和初春的情热都早成为过时的货色了。[47]
被时尚、洋气氛围包围的王府井俨然已经成为北京都市景观与摩登生活的“代言人”。而反观离此并不太远的天桥,则呈现出像似另一个世界的粗鄙景象,飞扬的尘土与污浊的气味给天桥的不同游览者留下了共同的印记:
天桥的暴土永远是飞扬着,尤其是在游人拥挤的时候。虽然也有时,暴土会稍为灭迹,然而这也只是在黄昏的一刹那,是极短暂的时间。在午间,游人们是兴奋的来到这里。同时,暴土也飞扬起来。汗的臭味、薰人的气息、还有脏水被日光所蒸就兴奋的发的恶味,是一阵阵的随着风飘过来,送到每个人的鼻孔里。这气味的难闻,会使人呼吸都感觉着窒塞。[48]
同样,“一股葱蒜和油的气息”出现在了作家姚克对于天桥的描述文字中,他称天桥为“高等华人所不去”、“北平下层阶级的乐园”。[49]“除却了一般失业的工人、退伍的士兵、劳苦大众及小商人等,摩登男女是绝少往游的”。[50]当时《世界日报》也介绍说天桥“地方虽然大,空气颇不好”。[51]因此,这里很难发现“绅士的少爷小姐们”的足迹,“他们怕灰土的污染,怕臭气的难闻,怕嘈杂的侵扰,他们是不愿看这些贱民,这些低级的艺术,这些缺少甜蜜味的剧本。”[52]民国时期,天桥一直被视为北京城内贫贱、卑微与肮脏的符号,是“下等人”的聚集之地,是自恃为“上等人”不愿去的地方,“天桥也就和伦敦的东区(East End)一样,是北平的贫民窟”。[53]那里的世界由许多散落着的布棚组合起来,那里的人群脸色多是“焦黑”或是“菜黄色”,他们从天桥中走出就像从“垃圾堆里”、“魔窟里”走出来一样。对于那些“美国绅士化的先生”和“擦巴黎香粉的小姐们”而言,天桥就像“谜一样”![54]《大公报》则直接对比了东安市场与天桥:
市场是有钱人们的消闲地,和天桥正是分道扬镳,各不相犯。从平常你可以听到“天桥地方太脏”、“市场东西特贵”这一类的话就可以证明。东安市场,那里有西服装、咖啡馆、画片摊,台球社,说不出颜色的蒙头纱,不带中国字的样糖果。……“畅销洋货大本营”,真是实至而名归。[55]
东安市场确实处处弥漫着“洋味”和“贵族化”:
东安市场在东城,多异邦街房,所以处处都带出点洋味来,(素称东城洋化,西城学生化,南城娼尞化,北城旗人化)因为他处在一个洋化区域之地,所以就得受洋化的传染,市场里的买卖,有的是专为买卖外国人而设的(如古玩玉器等),商人们也都能说两名洋话,来来往往的洋主顾,可占全市场内三分之二,逛市场的中国人,也以西服哥儿,洋式的小姐太太为最多,看来东安市场真是有点洋味和贵族化。[56]
市场正门两旁壁上,有各种商店的广告牌子,都钉得满满的、一进商场门,路的两旁,楼房并立,大的玻璃窗橱中,都装满西洋皮鞋,东洋衣料,……唉!什么市场,简直是洋货推销场罢了,有的是成群结队的男男女女,穿着奇装异服,携手搅腕,他们都是些提倡洋货的忠实同志。[57]

民国时期的北京天桥
不过,在许多人的认知中,带有现代气息的王府井、东长安街并不能够代表北京的城市底色。1936年,一位作者在《宇宙风》杂志上称:“我总以为北平的地道精神不在东交民巷、东安市场、大学、电影院,这些在地道北平精神上讲起来只能算左道,摩登,北平容纳而不受其化,任你有跳舞场,她仍保存茶馆;任你有球场,她仍保存鸟市;任你有百货公司,她仍保存庙会。”[58]社会学家李景汉在1951年为张次溪出版的《人民首都的天桥》所做的长序中也提及:“真北京人不是住在皇宫里面的,不是住在六国饭店的,不是住在交民巷的,不是住在高楼大厦的,不是住在那些公馆的,也不是常到大栅栏买东西的士女,或常光顾八大胡同的大人先生们”。[59]
而天桥则深刻嵌入了北京百姓的日常生活,亦被视为底层社会百相的重要展示地。《北平旅行指南》称:“天桥为一完全平民化之娱乐场所,亦即为北平社会之缩影”。[60]更有称天桥为北平大众的“情人”:
天桥是大众的情人,虽然脸子丑,可动摇不了爱者心。……在大众的眼里,这情人是金子,是宝贝。丽颜解不开恋结,装帧治不饱饥饿。只要她小心儿公平,大众就安慰。被生活压扁了的人,满怀着需求温暖,这情人正不羞涩地张开手臂,让那些粗野的魂灵拥抱;这情人正不吝啬抛洒着爱露,使那些污秽的口齿芬馨。柔情惑住了一头头的豹,你说卑弱的大众,不爱她,又爱谁?天桥便是以圣处女博爱的姿态,给你一个烈火似的照面。不论春花或秋月,不计清晨与黄昏,无一日,这儿不是一对挤,无一时,这儿不是一片嚷!估衣摊、京戏园、坤书馆、把戏场,声的嘈杂与人的喧嚣,整个暴露小世界的混乱,也整个暴露了这民族依旧是一盘沙。[61]
王伯龙在为张次溪《天桥一览》所作序言曾言:“天桥者,固北平下级民众会合游息之所也。入其中,而北平之社会风俗,一斑可见。……四郊人民,遂以逛天桥为惟一快事”。齐如山在为此书所做的序言中也强调了这一点:“今日之天桥,为北平下级社会聚集娱乐之所,以其可充分表现民间之风俗,于是外人游历,亦多注意于此,乃与宫殿园囿,等量齐观,其重要从可知矣”。为此,他建议,“有市政之责者,固应因势利导,推行改进。举凡卫生风化诸大端,若者取缔,若者改良,使下级民众,奔走终日。藉此乐园,得少游息,以调整其身心,节宣其劳苦,可为施政布化之助,毋为游情淫逸养成之所,以贻讥于外人。”[62]北平市社会局确也曾有在此设立民众乐园的计划,通过政治与教育双管齐下,以期改进区域秩序与市容观瞻。
不过,天桥地区的情况一直没有得到太多提升,日军占领北平之后,一些日本文人多次探访天桥一带,在他们的笔下,天桥区域仍然是“脏”、“穷”、“乱”、“俗”集中的地方,作家小田岳夫的《紫禁城与天桥》集中代表了这批日本文人对天桥的观察与体验:
与紫金城的庄严、华丽相比,这里是到处是污秽、卑俗,……其他地方随着文明的推移多少呈现出一些变迁,而与之相比,好像只有这里未被时代大潮所冲刷,保存着许多昔时的模样。事实上,这里处于没有电灯设备、开场只限于白天的状态,不论是杂耍的性质,还是胳膊纹着刺青、目光怪僻的无赖流氓之戏法、杂技演员仿佛从《三国志》中走出之感,都让人不由得产生一种地球虽在横向转动,我们却在纵向意义上逆时而生的奇异之感。……北京内城区之美与民众实际生活水平之低乃是大相径庭。说到如梦如诗般的北京城,有人也许会将生活其中的人也加以诗化想象。诚然,北京民众与其他城市的人比较起来,沉稳大方,但满街上来往的是破衣车夫,居民就像所有中国人一样,是彻底的实利主义者。我又想到了杭州西湖等巧妙利用了自然而造就的风景、上海租界等在社会生活的基础上形成的城市,感觉北京城之美是与民众生活、自然毫无关系的、尚未从古时王者之梦的遗迹中迈出一步的、幻影般虚幻之美。我想,这里有着北京的巨大矛盾。[63]
小田岳夫与齐如山都同时提到了北京的宫殿与天桥,两者的巨大对比呈现出的是北京城深刻的矛盾性,然而,这又是无法否认的真实,在两个相距并不远的城市空间内部彼此独立而鲜活地存在着,二者都是北京,城市内部的割裂性在王府井与天桥的对比中表现的最为直观。
民国时期,基于较低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北京的城市建设在空间上存在着明显的不均衡性,不同区域之间的城市景观形成鲜明对比。王府井周边的东长安街地区是北京最早开启城市化进程的区域,也是最能体现民国初年北京都市繁华的典型区域,“街道宽阔,清洁异常。若远立南端,遥望北瞻,则楼房林立,高耸霄汉,树路花草,云错其间。夜晚电灯悉明,照耀有如白昼,直有欧风美景。不若他处房屋矮小,街道污秽,人声嘈杂,一种腐败现象也”[64]。与此邻近的崇文门一带“行人拥挤,买卖发达,晚间电灯悉明,照耀如同白昼,夏间凉棚阴密,且多系楼房,一洗前清之旧观也”。[65]
到了1930年代中期,随着都市的进化,“王府井大街及东西单牌楼一带则完全向于立体派与现代都市派的设备了”,“东长安街多少是带有几分外国风味的,因为在它的附近的环境完全是洋味的,像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墙界,近代化建筑的北京饭店,中央,长安等大饭店,所以这里修建得很整齐的,将来要等东长安街的牌楼改建好了,怕是会更美观!”[66]1927年,北京大学政治学教授彭学沛在一个黄昏时分驱车经过东长安街所感受到是:
左边是一座摩天的高楼,无数的光明映照着满天的星斗。绿窗里,望得见金发的美人,想必是,坐对着盈盈的红樽。可是呀,千万别望到视平线以下!
右边是异邦人的管区,鳞列栉比的都是琼楼玉宇,青青的,廻环蔓延的藤萝,细细地,传出悠扬宛转的清歌。可是呀,仍然别望到视平线以下![67]
在那些摩天高楼、金发美人、宛转清歌之外,仍有一处“视平线以下”的那个我们没有看到的世界,作者虽未明确言及,但想必与眼前呈现的景象存在着巨大反差。
民国北京是一个异常纷繁与复杂的城市个体,不同群体并不能够共同分享同一座城市的相同记忆。对于王府井与天桥而言,二者都是外人认知民国北京的重要载体与媒介,如果只以一点观察北京,必然影响人们对城市的基本感知。1927年,从上海来的作家叶灵凤对北京发出感叹:“当我从东交民巷光泽平坦的柏油大道上走回了我们泥深三尺的中国地时,我又不知道那一个是该咒诅的了”。[68]几年之后,另一位从南方来到北京的作家钱歌川也有如此感受:
惯在北平王府井大街或东交民巷一带走动的人,他们是不会知道人间有地狱的。一朝走到天桥,也许他们要惊讶那是另外一个世界。殊不知那正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基础,我们这个人间组织的最大的成分呢。[69]
然而,情况似乎没有太大改善,十几年之后的1948年,当一位刚刚见识到王府井、东交民巷那样街道的游客来到天桥周边时,所见所感与钱歌川如出一辙:
我真是一个天大的傻瓜,我原先以为北京城只有像王府井东交民巷那样的街道,很替我们的文明感到荣耀,想到自己能生活在这样清洁高贵的城市里,不禁有些飘飘然了。现在却忽然从半空中跌下来;这算是什么都市!这样肮脏破烂的地方,连我们的乡下都不如呢。 [70]
需要指出的是,王府井与天桥的区域环境差异巨大,但并非没有交集,商业场所的开放性与流动性仍然在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消费空间中部分存在。在天桥,虽然少见所谓的上等阶级,但并非完全绝迹。进入1930年代之后,天桥的规模不断扩大,经营环境也有改良,一些演出场所“渐趋文明”,“非复昔时之简陋矣”,“而往游者非完全下层市民,至中上级亦有涉足其间者。”[71]张恨水小说《啼笑因缘》中很会游历的富家子弟樊家树,因为玩遍了北京的名胜古迹,于是“转而到下层人士常去的天桥游玩”,由此还发展出一段凄婉的爱情故事。[72]同样,在消费主义大潮兴起的过程中,王府井地区经过不断发展,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单一的消费场所,而逐渐演化为外人到京后争相浏览、参观的一处都市标志性新景观。以东安市场为例,虽然其以“高端”为定位,但来此游逛者也包含了其它阶层的人群,“上中下三等俱全,而其中尤以学生为最多,所以一到放假的日子,人便会多得拥挤不动。远道来京的人们,因为震于‘市场’的大名,也一定要去观观光。”[73]作为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商业街区,二者并非彼此排斥而是非竞争性并存。
余论
王府井与天桥两种城市景观的生成,实际上也是近代北京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一种历史表现。清代北京内城代表着权力、等级与秩序,外城则容纳了更多民间市井社会的生活内容,“内外城之间的城垣分辨出两个城区,造就两类城市社会,外城的存在,调整、缓和了京师的森严气氛,增加了京师城市社会的世俗性、丰富性。”[74]进入民国之后,皇权解体,北京内外城显性的地理边界逐渐被打破,但自明清以来一直存在的隐性的城市空间的等级差异延袭了下来,内外城在社会结构意义上的等级区分仍未有根本性改变,官方的主导、资本的驱动以及财富的聚集效应仍然维持着内城在北京城市格局中的核心地位。王府井大街地处京城传统的达官显贵聚居之地,且比邻东交民巷使馆区,集聚众多高档洋行与外资金融机构,诸多因素决定了其“高端”、“洋化”的商业形态。而天桥地区作为北京的外城,缺乏近代化的市政基础设施,地价与房租明显低于内城。这里三教九流、贩夫走卒、倡优皂隶,无所不包,成为城市贫民的主要聚居地。
王府井与天桥的差异并不仅仅是两个商业街区、两种商业模式或城市景观的差异,背后折射的是民国北京城市化进程中的巨大鸿沟以及社会阶层难以弥合的裂痕。因此,表现城市内部的多样性,是城市史研究的基本任务。只有兼顾不同来源渠道、不同类型的史料并加以综合辨析,才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后来者对城市书写的主观选择。
近年来,“民国热”不断升温,“民国范”被不断提及,浓重的怀旧气息与个体化的私人叙述构筑了民国的“黄金时代”。实际上,这种现象主要是当代人对逝去岁月的一种“记忆投射”,是借助历史资源对现实社会诸多现象进行的一种“柔性反抗”。他们通过选择性收集相关史料文字,构建了一个主观性很强的“想象世界”。以北京为例,当时大量文人、知识分子借助于文字表达方面的优势,他们的相关记忆与感性描述成为了构建“民国北京”的重要史料来源。但是,这类群体当时无论在经济地位还是在社会地位上,都属中上层群体,不仅在地域文化背景上与传统北京的普通平民有很大隔膜,在日常生活经验上也有诸多差异。他们那些带有浓重个人化色彩的散文性文字往往容易放大民国北京古朴、诗意的一面,对大部分底层群体的生存状态“视而不见”或“选择性失明”,这也反映出文学作品作为史料的使用限度,它们还不能代替当时官方以及一些社会学家所开展的各种社会调查数据。
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民国北京”,任何建立在单一史料来源基础上的城市叙事模式如同盲人摸象,都需要进行系统反思。城市史研究有多重内容、多重路径,城市阅读、城市书写是城市史研究中一种非常重要的表现方式,因阶级、种族、性别、年龄及文化水准等方面的差异,不同的观察视野,呈现民国北京不同的城市面孔。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真正进入城市内部,将那些被掩盖在统一表面之下的矛盾性与割裂性更多地表现出现,可能更加符合逝去时代的基本特征,亦是城市史研究的应有之义。正是不同叙述中的差异甚至矛盾构建了民国北京的多维面相,这几乎适用于所有城市。
民国北京,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既是古朴的,又是欧化的;既是贵族的,又是平民的;既是高尚的,又是卑微的。具有巨大矛盾性的不同事物彼此共存于同一个城市空间中,这不仅适用于民国北京,而且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地域范围内,同样如此。
(本文初刊于《学术月刊》2016年第12期。)
[①]董玥在《民国北京城·历史与怀旧》中专门设有一章,探讨了民国北京不同消费空间与市场等级的对应关系,以及由消费行为所构建的社会阶层划分等问题,重点涉及到王府井与天桥(三联书店,2014)。岳永逸在《空间、自我与社会:天桥街头艺人的生成与系谱》中,多次触及天桥作为城市边缘地带所具有的“贱”、“脏”、“穷”、“乱”等典型的社会特征(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陈平原曾提出,以胡同为代表的老北京与以大院为代表的新北京,存在着裂缝;紫禁城的皇家政治与宣南的士大夫文化之间,也有巨大的差异,王公贵族与平民百姓并不分享共同的城市记忆(《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北京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相关研究还可参见王均《现象与意象:近现代时期北京城市的文学感知》,《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2期;王升远《“文明”的耻部——侵华时期日本文化人的北京天桥体验》,《外国文学评论》,2014年第2期。
[②]马芷庠编著、张恨水审定:《北平旅行指南》,北平:经济新闻社,1937,第331页。
[③]《东安市场现办章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三十二年创办东安市场史料》,《历史档案》,2000 年第 1期。
[④]兰陵忧患生:《京华百二竹枝词》,路工编选:《清代北京竹枝词(十三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第129页。
[⑤]郭海:《东安市场记》,林传甲编纂:《京师街巷记》,“内左一区卷三”,武学书馆,1919,第1—2页。
[⑥]徐珂:《增订实用北京指南》,第一编:地理,第5页;第八编:食宿游览,第22—23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
[⑦]《平市人心渐趋安定,将重觅享乐生活》,《世界日报》,1933年6月2日。
[⑧]马芷庠编著、张恨水审定:《北平旅行指南》,第331—332页。
[⑨]娄学熙:《北平市工商业概况》,北平市社会局编印,1932,第684页。
[⑩]铢庵(瞿宣颖):《东安市场》,《申报月刊》第2卷第10号,1933年。
[11]崇普:《王府井大街记》,林传甲编纂:《京师街巷记》,“内左一区卷三”,京师武学书馆,1919,第5—6页。
[12]《北平市况:南城的繁荣已被东西城所夺》,《大公报》,1933年3月2日。
[13]赓雅:《北上观感·自治风云中之慘象》,《申报》,1936年2月9日。
[14]马芷庠编著、张恨水审定:《北平旅行指南》,第10—11页。
[15]见张次溪《天桥丛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第1页。关于“天桥”名称起源,还有一种说法是源自附近的天坛。两种说法其实差异不大,实际指向都赋予了“天桥”一层特殊的权力背景与象征。
[16]张次溪编:《天桥一览·齐序》,中华印书局,1936,第1页。
[17]震钧:《天咫偶闻》,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第135页。
[18]张次溪编:《天桥一览·齐序》,中华印书局,1936,第3页。
[19]张次溪编著:《天桥丛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第8页。
[20]张次溪:《人民首都的天桥》,修绠堂书店,1951,第12页。
[21]秋生:《天桥商场社会调查》,《北平日报》,1930年2月16、17日。
[22]张次溪编:《天桥丛谈》,北京修绠堂书店,1951,第11页。
[23]张次溪编:《天桥一览·齐序》,中华印书局,1936,第4、1、3页。
[24]陈宗藩:《燕都丛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第641页。
[25]秋生:《天桥商场社会调查》,《北平日报》,1930年2月16日。
[26]马芷庠编著、张恨水审定:《北平旅行指南》,第260—261页。
[27]黄宗汉主编:《天桥往事录》,北京出版社,1995,第43—44页。
[28]慈:《天桥素描》,《市政评论》,第3卷第16期。
[29]马芷庠编著、张恨水审定:《北平旅行指南》,第10页。
[30]易顺鼎:《天桥曲》,转引自张次溪编著《天桥丛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36,第35页。
[31]张次溪编:《天桥一览》,中华印书局,1936,第12页。
[32]慈:《天桥素描》,《市政评论》,第3卷第16期。
[33]马芷庠编著、张恨水审定:《北平旅行指南》,第260—261页。
[34]易顺鼎:《天桥曲》,转引自张次溪编著《天桥丛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36,第35—36页。
[35]衷若霞:《天桥》,《宇宙风》第21期,1936年7月16日。
[36]张次溪编:《天桥一览》,中华印书局,1936,第13页。
[37]严景耀:《北京犯罪之社会分析》,《社会学界》,1928年第2期。
[38]张次溪编:《天桥一览·王序》,中华印书局,1936年,第1页。
[39]李大钊:《新的!旧的!》,《新青年》第4卷第5号,1918年5月15日。
[40]铢庵(瞿宣颖):《北游录话(七)》,《宇宙风》第26期,1936年11月1日。
[41]沈从文:《二十年代的中国新文学》,《沈从文全集》第1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第377页。
[42]味橄(钱歌川):《游牧遗风》,收入其《北平夜话》,上海:中华书局,1936,第99页。
[43]老向:《难认识的北平》,《宇宙风》第19期,1936年6月16日。
[44]朱自清:《南行通信》,原载《骆驼草》第12期,1930年7月28日。引自朱乔森编《朱自清散文全集》(下),江苏教育出版社,第543页。
[45]林语堂:《京华烟云(下)》,《林语堂名著全集》,第2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第420页。
[46]孟起:《蹓跶》,《宇宙风》第23期,1936年8月16日。
[47]木易:《东安市场巡礼》,《老实话》第10期,1933年。
[48]张次溪编:《天桥一览》,中华印书局,1936,第12—13页。
[49]姚克:《天桥风景线》,姜德明编:《北京乎:现代作家笔下的北京(1919—1949)》,上,第353—357页。
[50]程文蔼:《北平社会经济的一瞥(续)》,《申报》,1933年7月24日。
[51]《平市人心渐趋安定,将重觅享乐生活》,《世界日报》,1933年6月2日。
[52]衷若霞:《天桥》,《宇宙风》第21期,1936年7月16日。
[53]味橄(钱歌川):《游牧遗风》,收入其《北平夜话》,中华书局,1936,第102—103页。
[54]文:《天桥印象记》,《老实话》第6期,1933年。
[55]卡员:《故都印象》,《大公报》,1932年10月15日。
[56]云:《东安与西单商场》,《市政评论》第3卷第15期。
[57]王天又:《北平东安市场》,《同钟》第1卷第11期,1935年。
[58]张玄:《北平的庙会》,《宇宙风》第19期, 1936年6月16日。
[59]张次溪:《人民首都的天桥》,修绠堂书店,1951,第2页。
[60]马芷庠编著、张恨水审定:《北平旅行指南》,第260页。
[61]刘芳棣:《天桥:北平大众的情人》,《中央日报》,1936年7月7日。
[62]张次溪编:《天桥一览》,中华印书局,1936,第1、3—4页。
[63]小田岳夫:《紫禁城与天桥》,竹山书房,1942,第50—52页。引自王升远《“文明”的耻部——侵华时期日本文化人的北京天桥体验》,《外国文学评论》,2014年第2期。
[64]宋世斌:《东长安街记》,林传甲编纂:《京师街巷记》,“内左一区卷二”,武学书馆,1919,第6—7页。
[65]崔扬名:《崇文门大街记》,林传甲编纂:《京师街巷记》,“内左一区卷二”,京师武学书馆,1919,第4页。
[66]张麦珈:《北平的新姿态与动向》,《市政评论》第3卷第20期。
[67]彭学沛:《黄昏驱车过东长安街》,《现代评论》第4卷第84期。
[68]叶灵凤:《北游漫笔》,《天竹》,上海现代书局,1931,第49—61页。
[69]味橄(钱歌川):《游牧遗风》,《北平夜话》,第105页。
[70]青苗:《陶然亭访墓记》(1948年),《如梦令——文人笔下的旧京》,北京出版社,1997,第589页。
[71]马芷庠编著、张恨水审定:《北平旅行指南》,第260—261页。
[72]张恨水:《啼笑因缘》,安徽文艺出版社,1985,第1页。
[73]太白:《北平的市场》,《宇宙风》第21期,1936年7月16日。
[74]唐晓峰:《明代北京外城修建的社会意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都市繁华——一千五百年来的东亚城市生活史》,中华书局,2010,第138页。
推荐阅读
- 上一篇:中国虚拟货币排名2018
- 下一篇:买卖虚拟货币欧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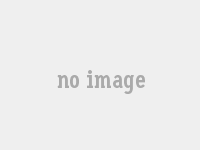
-
奥斯卡虚拟货币怎么买(BUCKS是什么)
1970-01-01
【摘要】 作为民国北京两处重要的城市空间与商品交易场所,王府井大街与天桥地区代表不同的商业形态,同时也是城市风貌与社会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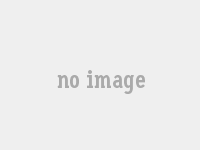
-
游戏虚拟币交易平台?虚拟货币交易用什么软件
1970-01-01
【摘要】 作为民国北京两处重要的城市空间与商品交易场所,王府井大街与天桥地区代表不同的商业形态,同时也是城市风貌与社会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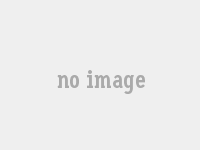
-
陕西虚拟货币挖矿举报平台,12369举报范围
1970-01-01
【摘要】 作为民国北京两处重要的城市空间与商品交易场所,王府井大街与天桥地区代表不同的商业形态,同时也是城市风貌与社会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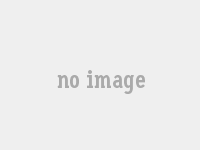
-
乡镇虚拟货币挖矿排查情况 (虚拟货币)挖矿犯不犯法?
1970-01-01
【摘要】 作为民国北京两处重要的城市空间与商品交易场所,王府井大街与天桥地区代表不同的商业形态,同时也是城市风貌与社会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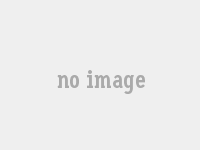
-
最近大涨虚拟货币,虚拟币最近为何大幅上涨?
1970-01-01
【摘要】 作为民国北京两处重要的城市空间与商品交易场所,王府井大街与天桥地区代表不同的商业形态,同时也是城市风貌与社会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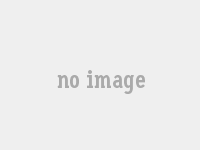
-
虚拟货币外围资金是什么,外围指数怎么还在变动
1970-01-01
【摘要】 作为民国北京两处重要的城市空间与商品交易场所,王府井大街与天桥地区代表不同的商业形态,同时也是城市风貌与社会生...